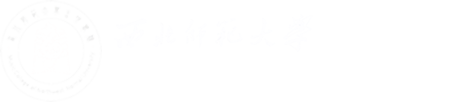“奏鸣·论乐”上海音乐学院与西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学术交流分享心得(一)
拿来莫忘坚守,洞彻兼具融合
2019年3月26日上午,西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的音乐厅高朋满座,群贤毕至。来自上海音乐学院的伍维曦教授进行了一场题为《江声浩荡自天外——傅雷艺术观念的“国粹”与西学》的学术讲座,不仅向大家推介了一位人品高贵、学贯中西的巨匠,还通过一系列年代稍远却又不可遗忘的客观事件阐发了诸多学术观点。其构思独出机杼,论域纵横捭阖,学理蕴藉丰厚,思想意味深长,令人折服。
言为士则,行为世范。伍教授突出了傅雷除翻译家之外作为文艺评论家的重要地位,指出了傅雷文论之高、之精,皆呈现了世界的真髓。傅雷的评论涉及到了中西文学(如对张爱玲的早期评价)、美术和音乐的方方面面。作为音乐评论家和美术评论家两个不同身份的傅雷,即激进的西化论者和保守的国粹派,两者并立,且作用于同一。
激进的西化论者体现在傅雷对于西方近世音乐的推崇备至。他不仅翻译了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还撰写了相关长文。而对于中国传统民间音乐而言,从其著述中不难窥探,鄙夷与贬斥之词占据上风。无论是西方之赞美,还是传统之喟叹,傅雷并非仅仅驻足于个人之偏见,也竭力洞察了客观之现实。外现的幼稚、隐藏的缺陷等等带来了诸多束缚,最终造成了中国传统民间音乐理论与技巧上的乏善可陈。此种情形下的“落后”与西方音乐的“先进”不仅是随波逐流下的苟同,也是当时关注音乐问题的知识分子在将中国固有音乐和欧洲“古典”音乐进行对比后所做出的判断。
保守的国粹派则体现在傅雷对于“传统主义者”的严格践行。他曾在一封信中精到地分析了中国绘画与欧洲绘画在技法与美学上的差异,指出中国绘画中线条表现力的丰富程度以及种类的界定非西洋画所能比拟。其一笔、一点皆有其深意,如此一来,整体之质感犹如美之集合,浑然天成。此外,中国绘画之用墨也颇有讲究,其范式与方法也体现了不同的中西艺术观。而在傅雷眼中,近代中国画家之优劣自有其取舍。对于石涛、黄宾虹之欣赏,对于张大千之蔑视,皆未作修饰,跃然纸上。
“激进”与“保守”式的傅雷在伍教授的解读下略显不可调和,但又各树一帜。继而引发了以下几个问题的探讨。其一,经典与文脉。傅雷之思想分野明确,应持有一种“本位性”理念对待中国固有文学艺术中古典文脉成分,并以此去反观西方文化中的对应物,而对于其它,则以进化论立场视之。此外,对于承载欧洲核心人文价值的西方作品应予以观望。其二,“落后”与“先进”。其本身顺时而行,顺势而行,所处时代的时代思潮与艺术观念,皆在不同程度上进行着扬弃。其三,士人与传统。其观念之维度不仅基于伦理,还取决于审美。他那纯粹的“儒生”和“古人”形象使得他对中国绘画研究深入,而他那扎实的西方美术训练与根底也使其触及了绘画的精髓。
正如遥远的古希腊和春秋战国时期众多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他们之所以没有被接踵而至的的时代潮流所忘却,正是因为他们在当时的时代便可以各执己见、攻过箴阙,从而推陈出新,缔造出醒世恒言。傅雷用犀利的言辞击中了众多“伪善艺术家”的要害,点醒了毫不知情的芸芸众生,让“艺术作品乃艺术家个体人格之外化”的观念深入人心。他那绘画中一以贯之的传统自信,音乐中深信不疑的西方凝视,使其心底的那份执着愈演愈烈,两者伴随其对于经典的定义以及浪漫主义情怀的滋养,矛盾日渐消解,最终实现了世所罕见的融合。总体而言,其“器”深广,难测量也。他用毕生之期限为我们种下了一棵棵善于思考的芦苇。
江声浩荡,寒风凛冽。“西风烈”,拿来主义便充斥耳边,传统之优越感将损失殆尽,古典之文脉也终将洗劫一空。因此,拿来莫忘坚守。“东风烈”,痼疾继续得以“蔓延”,时代之“寒流”继续得以侵袭,徜徉于盈尺,拘泥于陈法,历来之经典终将朝不保夕,被声势浩荡之巨浪所湮没。因此,洞彻还需融合。伍教授以傅雷为例,由个案得以拓展和延伸,让我们浏览了一位大师的传奇人生与思想建树,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个时代的悲伤与勇气。告诫我们欲穷千里,需在时代里缓慢行走,细细思量,因为无论哪个阶段的个人或事物都有可能面临不同的境遇,即使是我们的传统民间音乐,它终有一日也将开出奇异之花,绽放于世界。因为我们深信:早成者未必有成,晚达者未必不达。
(撰文:方坤,审校:马瑜慧)
载歌载舞,满园欢喜
--听《唐代敦煌壁画婚嫁图中的乐舞文化——莫高窟第445窟为例》有感
上海音乐学院与西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奏鸣·论乐”学术艺术实践交流活动于26日上午拉开了帷幕,其中硕博学术论坛是一大特色,即融合了各专业学术前沿的探微,又包含了西北地域传统音乐文化特色的探究,为我们带来了一场学术盛宴。
西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二年级研究生吴林烜的学术论题突出了地域性文化特色,她以敦煌莫高窟第445窟《婚嫁图》中的小型乐队为主要研究对象,并结合相关文献对比考证,从该窟《婚嫁图》中的乐人、乐器及乐器组合情况进行了介绍。
通过报告,我们了解到敦煌壁画中的婚嫁图主要存于《弥勒经变》中,以表现“女子五百岁出嫁”的佛经内容。因各个洞窟壁画所要展现的主题不同,因此壁画中没有一副相对完整的婚嫁仪式过程图,但把众多洞窟不同场景的婚礼仪式连接起来,便就构成了一副完整的婚嫁仪式过程图。可分为婚礼前程序、婚礼中程序和婚礼后程序。而敦煌壁画中则常描绘的是婚礼中的某个程序,例如铺帐、进喜房、撒帐、遮扇等环节,将其绘制为具有象征意义的图像。
婚嫁乐舞图的呈现一般是由少量的乐伎、舞伎构成,其形式属于敦煌古代乐舞中的世俗乐舞类。在婚嫁乐舞中,乐队规模较小,一般为民间小型乐队为主。从乐队演出形式上来看,有站立式和坐卧式两种形式,并以前者居多;从乐器的演奏形式来看,有吹管乐器、打击乐器、弹拨乐器三类,前两类多相互配合使用,使用较为广泛,后类次之。
婚嫁乐舞中的舞技主要以世俗乐舞伎为主,通常没有太多讲究,有时也会出现百戏。敦煌古代乐舞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悠久漫长的过程,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军事战略地位,敦煌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因此敦煌音乐包含了多种民族音乐的成分,不仅包括本土乐舞、中原传统乐舞,还包括西域各少数民族乐舞。例如婚嫁乐舞中就有舞伎挥跳吐蕃族的舞蹈,就是现今藏族舞的姿态。其壁画乐舞图中的乐伎、舞伎载歌载舞,满园欢喜,将千年之前热闹红火的婚嫁场景穿越呈现。
从上古时期开始音乐和舞蹈已呈现出乐中有舞,舞中有乐,密不可分之态,在称谓上常常乐舞不分家。敦煌壁画中千姿百态的乐舞图像为我们提供了翔实了佐证,对我们更加深入研究古代乐舞的发展过程提供了一个更加明晰的图像资料。
(撰文:朱爱,审校:马瑜慧)

中国器乐活化石——“楚吾尔”的再探讨
发言人:马毓青
“楚吾尔”是图瓦人特有的吹管乐器。马毓青同学的发言以一段“楚吾尔”的吹奏视频开始,向我们简单介绍了“楚吾尔”的演奏形式及其发声原理,之后分别从“楚吾尔”的研究开端、田野调查和分析再探讨三个部分,对“楚吾尔”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第一部分,介绍了“楚吾尔”的研究开端,此乐器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两位会吹奏冒顿楚吾尔的民间艺人。2005年,中国图瓦人中唯一会吹奏“楚吾尔”的叶尔德西,受邀到北京参加专门为“楚吾尔”举办的一系列学术活动,至此引发了一股“楚吾尔”研究热潮。2008年“楚吾尔”被列为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第二部分,马毓青同学通过田野调查中一些图片材料的讲解,详细的介绍了图瓦人的历史、宗教、节日、传统乐器以及他们特有乐队的演奏形式。
第三部分,她讲解了“楚吾尔”的形制和演奏原理,乐器主要是由非常稀有的“芒达勒西”制作而成。其演奏原理为,先从喉咙缓缓发出一个持续长音,继而带动管身按孔发出高低不同的泛音旋律,两个声部同时发响。“楚吾尔”只有三个音孔,乐器的演奏与表现完全是靠演奏者气息和按孔决定的。楚吾尔吹奏的音乐,讲究贴近大自然的声音,也就是要求族人要会运用“楚吾尔”去模仿自然界中听到的声音,并以此与自然界沟通。
最后她为我们讲述了关于“楚吾尔”的发展现状,并举例说明运用“楚吾尔”乐器进行的一些新尝试。此次报告,马毓青同学对田野调查中收集到的视频、音频以及照片材料进行了分析讲解,使我们更加全面的了解图瓦人特有乐器——楚吾尔。她长期深入田野,研究深入细致,研究资料生动详实,她的刻苦精神,深深感染着我们在坐的每一位同学。
(图文:马晶雨,审校:马瑜慧)